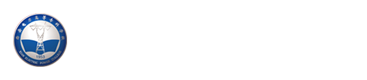中国现代文艺史上,有许多名家,丰子恺(1898年11月9日—1975年9月15日)是其中十分特别的一位,如果少了他,中国现代文化的生态,将因此而大大失衡。
这不仅因为他是一个通才,在文学、绘画、书法、音乐、翻译等领域均有很深造诣,为中国现代的美育事业立下汗马功劳,更因为,他是一个禀赋奇异、风骨高迈的传奇性人物,用日本著名汉学家吉川幸次郎的话说,他是现代中国“最像艺术家的艺术家”。
“子恺漫画”与“缘缘堂随笔”,是丰子恺留给现代中国的两件瑰宝,时过境迁,依然熠熠生辉,滋养了几代中国人的灵魂。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有“为人生而艺术”的“社会派”(文学研究会发起)和“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派”(创造社发起)。丰子恺是文学研究会特别推出的漫画家,甚至连“子恺漫画”的称号,都是该会重要人物郑振铎发明的,由此足以证明丰子恺的艺术与“人生”的密切关系。然而,丰子恺并不属于这一派,他的眼光,不经意间,便会穿透“人生”的表层,直抵人生的“根本”。准确地说,丰子恺对人生社会的关注,是出于佛家慈悲为怀的“护生”信仰。
相比之下,丰子恺与自我表现,崇尚天才的“唯美派”距离更远,尽管他最强调艺术“趣味”。细审之下,其“趣味”的核心,是超越艺术形式的“童心”“真心”和“本心”。因此,如果一定要对丰子恺的艺术创作下一个定义,只能是“为生灵而艺术”。它的存在,意味着现代文学史上除“社会派”“唯美派”“革命派”之外,还有一个隐性的“生灵派”(属于这一派的,有许地山、叶圣陶、冰心、废名等人),丰子恺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在风雷激荡的20世纪中国,这一派不合时宜,难成气候,却不绝如缕。时过境迁,越来越显示出它的价值。
佛缘与艺缘
丰子恺一生结二缘——佛缘与艺缘。于是派生出一个麻烦的问题:艺术与宗教,情状虽相似,本质却有差别,各有不同的价值体系与精神诉求。丰子恺因此难免经受复杂的内心矛盾与纠葛,正如《忆儿时》描写的那样:而立之年的丰子恺,津津有味地回忆童年时代养蚕、吃蟹、钓鱼的趣事,最后总是上升到“杀生”的高度,一面使他“永远神往”,一面使他“永远忏悔”。这种矛盾纠葛,在《陋巷》(1933年)中有集中的表露。
“陋巷”是圣人品格的象征,取自《论语》中“居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典故。而今,守在此地遥接衣钵的,是通儒马一浮。文章记述“我”与马一浮的三次见面,禅意深致。通过字里行间,可以看出,马一浮在丰子恺心目中是“教主”式的存在。第一次随恩师李叔同拜见马一浮,因听不懂两位长辈的北腔方言(马以不地道的北方音回应李的天津白),愧恨无奈中变成了一个尴尬的傀儡,却牢牢记住了马一浮的奇秉异相:“头圆而大,脑部特别丰隆,上眼帘弯成一条坚致有力的弧线,切着一面的深黑的瞳子”。
第二次见马一浮,是16年之后,受弘一法师的委托而去。这次丰子恺能够听懂马一浮的绍兴土白,心境却与之前大不一样:他刚刚失去母亲——从他孩提时代兼尽父职的母亲,丰子恺感到自己未能对母亲尽涓涘的报答之情,悔恨至极,心中充满了对无常的悲愤与苦痛,于是便堕入颓唐的状态。这无疑是接受开解,皈依上帝的最佳时刻。耐人寻味的是,丰子恺最终还是回避了大师的开解。其中这样写道——
M先生的严肃的人生,明显地衬出了我的堕落。他和我谈起我所作而他所序的《护生画集》,勉励我;知道我抱风木之悲,又为我解说无常,劝慰我。其实我不须听他的话,只要望见的颜色,已觉羞愧得无地自容的。我心中似有一团“剪不断,理还乱”的丝,因为解不清楚,用纸包好了藏着。M先生的态度和说话,着力地在那里发开我这纸包来。我在他面前渐感局促不安,坐了约一小时就告辞。当他送我出门的时候,我感到与十余年前在这里做了几个小时傀儡而解放出来时同样愉快的心情。我走出那陋巷,看见街角上停着一辆黄包车,便不问价钱,跨了上去。仰看天色晴明,决定先到采芝斋买些糖果,带了到六和塔去度送这清明日。但当我晚上拖了疲倦的肢体而回到旅馆的时候,想起上午所访问的主人,热烈地感到畏敬的亲爱。我准拟明天再去访他,把心中的纸包打开来给他看。但到了明朝,我的心又全被西湖的春色所占据了。
这段文字,将丰子恺彷徨于宗教艺术之间的复杂情愫展露无遗。此时的丰子恺,一方面感到“无常”加给他的压倒性痛苦和颓唐,另一方面又离不开艺术给予他的快感与慰藉,在双方博弈、难解分难的时刻,丰子恺选择了逃离,因为“西湖的春色”。
上一篇:营造尊师重教的良好环境
下一篇:超星移动图书馆正式开通上线了